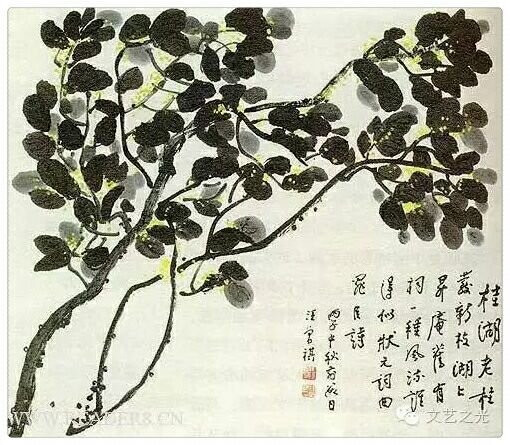
■汪曾祺在西南联大①
西南联大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丰碑和奇迹,汪曾祺就读的时间是1939年至1943年。他的大学读了5年,最终也只拿了个肄业证书。
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,抗日战争全面爆发。汪曾祺所就读的江阴南菁中学停课,其时他正上高二。为完成学业,曾辗转多地借读,亦时读时辍,其间曾跟随家人到离城稍远的乡下庵中避难(即小说《受戒》所写的那个庵)。随身所带除了备考所需的数理化教科书,只有屠格涅夫的《猎人日记》和《沈从文小说选》两书。汪曾祺曾言:“说得夸张一点,可以说这两本书定了我的终身。”其实远不止于此,定了他终身、让他走上写作一途的还有他的大学。
日军南侵,偌大的华北放不下一张书桌。北大、清华、南开合并组建临时大学,南迁至长沙,改为西南联合大学,继而又迁至昆明。在相对安全、条件十分艰苦的环境下办教育,传承文化火种,谱写出中国教育史上璀璨的华章。
从1938年至1946年,西南联大九年,培育出八千余名毕业生,扛起中国科学文化发展的大梁,为中华民族复兴作出卓越的贡献。其间流传至今的故事,折谢出的精神、风骨、人格是那般超然绝尘、爽然高举,令我辈无限神往慨叹。
1939年,汪曾祺辗转大半个南中国,经由上海、香港、越南来到昆明,报考西南联大。由于一路奔波,他得了恶性疟疾,住进医院,高烧超过四十度,几至病危。待刚刚能喝一碗蛋花汤,就晃晃悠悠进了考场,居然顺利考中。他报考的是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。
汪曾祺说西南联大各系学生各有特点,从外表上亦能看出个大概,中文系的男生多为“不衫不履”的名士派头。何孔敬的《长相思》一书中有一张李荣、汪曾祺和朱德熙三人的合影,大抵如此,三人均身着长衫、不修边幅的样子。如果说这还只是表面现象,那么汪曾祺骨子里也是个潇洒不拘、自由散漫的人。
他上课很随便,喜欢的就上,不喜欢的就不上。沈从文先生的课他都上——“各体文习作”是二年级必修课,“创作实习”“中国小说史”是选修课,他都选了。据他回想,沈从文并不擅讲课,声音小,操着很浓的湘西口音,不好懂。然而他又说要是能听“懂”的话,就会受益匪浅、终生受用。让汪曾祺体味深刻并在以后的写作实践中深有同感的是“要贴到人物来写”,这句话他算是读通透了。
闻一多先生的课他也喜欢。闻一多先后开过楚辞、唐诗、古代神话三门课。楚辞课上,闻先生先点燃烟斗,会抽烟的学生也可以点上(汪是会抽烟的学生之一),然后开讲:“痛饮酒,熟读《离骚》,乃可以为名士”。这个课前细节被后人广为传颂,汪曾祺是亲历者。他说上闻先生的课,“让人感到一种美,思想的美,逻辑的美,才华的美”。他盛赞闻先生讲唐诗“并世无第二人”,不蹈袭前人一语,是将晚唐诗和西方印象派画对比、用比较文学方法讲唐诗的第一人。
即便沈从文、闻一多两位先生的课在他看来精彩无比,汪曾祺也大大咧咧,从不记笔记。以至他后来不无遗憾地说:“我如果把沈先生讲课时的精辟见解记下来,也可以成为一本《沈从文论创作》。可惜我不是这样的有心人。”他对同学郑临川能把闻一多上唐诗的课整理出版成《闻一多论唐诗》佩服得不得了,说是做了件大好事。
但有的课不对路子,便不去上。他主动旁听过西语系教授吴宓的“中西诗之比较”,只听一节就放弃了,原因是他讲的第一首诗是:“一去二三里,烟村四五家,楼台六七座,八九十枝花。”他认为这未免太浅了。朱自清的“宋诗”课,他也不甚喜欢,理由是太严格。“他一首一首地讲,要求学生记笔记,背,还要定期考试,小考,大考”。这不太符合汪曾祺自由散漫的性情,便时常缺课,这给朱自清留下不佳印象,以至大学毕业后,中文系主任罗常培曾推荐他给朱自清当助教,被一口回绝:“汪曾祺连我的课都不上,我怎么能要他当助教!”
上课随便,读书也随性,这大抵是汪曾祺的大学生活。这个随性表现在两个方面,一是杂,一是不拘时间地点。杂到什么程度?用他自己的话说“从心所欲,随便瞎看”,连元朝菜谱类的书《饮膳正要》都看得挺仔细,可见博杂之极。当然还看了大量的西方文学、哲学作品,如纪德、阿索林、弗洛伊德、萨特、伍尔芙等等,都看过。也是出于随性,对于广为称道的列夫·托尔斯泰却始终提不起兴趣。直至晚年,汪曾祺认为,读杂书好处多多,对其创作有着多方面的积极影响。
看书不拘地点。茶馆、系图书馆、翠湖边上的图书馆都去,只是不愿去学校的大图书馆——那么多人正襟危坐的读书方式,他不乐意接受。他愿意去系图书馆看书,完全是因那里的自由,随便什么书,想看就抽下来看,不用经过借书手续,而且还可以抽烟。一次在系图书馆夜读,听得墙外坟地一派细乐之声,很是瘆人。
看书不分时间,黑白颠倒。他和历史系一位同居25号联大宿舍的舍友,几乎不曾谋面,原因是那个同学每天黎明即起,他则从不循规蹈矩,是个夜猫子。他说自己“差不多每夜看书,到鸡叫回宿舍睡觉”。有一段时间租住在民强巷,每晚看书写作到天已薄亮,听到邻居家的鸭子呷呷叫起来,他才睡去。可见他的吊儿郎当只是作息时间的不规律,对于读书和写作还是极用功和用心的。
自由还表现在教授们上课及学生们的选课上。据汪曾祺回忆,教授们想讲什么就讲什么,想怎样讲就怎样讲,无人干涉。教文字的唐兰先生开过《词选》,上课基本不讲,就是操着无锡腔,把词吟一遍。“双鬓隔香红啊,玉钗头上凤。——好!真好!”一首词就算讲完了。联大教授的课也都可以随意旁听……
教授们自由上课,学生自由选课、读书,学校都一样的宽容,没有条条框框的限制。除了一些基础性的课,大多数教授对学生要求不严,一般都是学期末交一篇读书报告即可。当然,读书报告重在有无独创性见解,而不是抄书。联大师生都有较大的自主性,这大概是这所学校能够培养出那么多杰出人才的原因之一吧。
汪曾祺对此深信不疑,他认为正是西南联大自由宽松的氛围造就了他:“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,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。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。”
当然也正是因为自由和随性,汪曾祺为此也付出了代价。因为体育、英语两门课不及格,他多读了一年大学;又因没按学校规定到前线做翻译,他没有拿到大学毕业证书。这让他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格外多了一些波折,吃了不少苦头。可见联大的宽松自由和严格要求是并行不悖的,这是否也是这所大学的魅力所在?(段春娟,汪曾祺研究者,山东财经大学副编审,主编《你好,汪曾祺》等)
《中国教育报》2016年11月26日第4版



